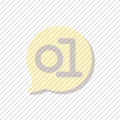熟諳星座的人里,有這樣一句話廣為流傳,「人固有一死,或死於天蠍,或死於摩羯。」想必一定有人被這兩個星座傷得太深,從某種程度上,這些傷有可能是咎由自取,雖然這兩個星座各有各的冷酷,但如果不去主動招惹,有些傷還是能夠避免的。
冬至過後,摩羯座冷酷登場,堅韌、隱忍、睿智,是摩羯座的標籤,這些特質能夠造就什麼樣的作家呢?西蒙娜·德·波伏瓦、傑羅姆·大衛·塞林格、村上春樹、沈從文、史鐵生、梁實秋、傑克·倫敦、埃德加·愛倫·坡、亨利·米勒等等,都是摩羯座,一時間卻難以找到明顯的共同點,但是,回溯他們的作品和人生,卻又都將摩羯座的特質發揮到了極點。
第二性

《第二性》被稱為西方社會裡女性的聖經,被譽為「有史以來討論婦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滿智慧的一本書」。在這本書里,波伏瓦提出了女性獲得經濟獨立的必要性,也強調了只有女性經濟地位變化才能帶來精神的、社會的、文化的等等後果,只有當女性對自身的意識發生根本的改變,才有可能真正實現男女平等。這本書首版時間是1949年,但是今天看來,依然符合時代需要,意識不發生徹底改變,其他一切都是空談。
提到波伏娃很難繞開薩特,但並不是薩特成就了波伏瓦,而是正因為她是波伏瓦,所以才選擇了薩特。在遇見薩特之前,波伏瓦已經在初戀雅克的映照下成為了自己。他們之間的差異,讓波伏瓦能夠義無反顧地放棄情感,而選擇理智。波伏瓦在《手記》里寫,「他接受奢侈和優遊的生活;而我,我需要不斷進取的生活!」這個時候,波伏瓦才18歲,對於不斷進取的生活,她有著明確的目標,「我習慣了刻苦工作,我需要有一個目標讓我去達到,有一部作品讓我去完成。」
如果按照如今入流的思路,波伏瓦有著典型的成功型人格,在堅定的目標推動下,她不會做出任何與其向左的選擇。選擇薩特也一樣,因為薩特不會跟她簽像別人一樣的婚姻契約,兩個人彼此獨立,適當的距離,才成就了後人所認為的終身伴侶。儘管兩個人在稱對方為伴侶的同時都曾有過各自的情人,但卻沒辦法否定這段關係的堅不可摧,甚至到了婚約都不能達到的程度。
沒有婚姻,但是有伴侶,有作品,波伏瓦過著不同次元的生活。之所以能夠放棄一些,而擁有一些,也正是因為對文字的執著。當年因為要去完成一部作品放棄的情感,換來了之後的許多作品,《名士風流》《第二性》《人都是要死的》《女賓》等等,她的創作不曾間斷,她關於女性獨立的主張,依然是很多女性心之所向。
關於波伏瓦,《戰鬥的海狸:西蒙娜·德·波伏瓦評傳》的作者達妮埃爾·薩樂娜芙這樣說,波伏瓦最大的榜樣作用就是:貴在堅持,堅持自己選擇並堅持自己作出的每一個選擇。
麥田裡的守望者

《麥田裡的守望者》首版於1951年,剛剛贏得二戰勝利的美國,物質、功利蒙蔽了人們的雙眼,精神世界漸趨荒蕪。《麥田裡的守望者》借主人公之口,對現實社會給予極大力度的批判,那個頭戴鴨舌帽,身穿風衣的少年霍爾頓成為眾人的擁躉。憤怒與焦慮是本書的兩大主題,但最本質的還是與成人世界的疏離。
作者傑羅姆·大衛·塞林格締造了這樣一位典型的反英雄,而他本身也是一個反英雄的典型。塞林格出生於紐約一個猶太富商家庭,15歲被送到賓夕法尼亞一所軍事學校,二戰期間,塞林格從軍,前往歐洲戰場從事反間諜工作。戰爭結束,塞林格退伍,回到紐約專心寫作。
《麥田裡的守望者》是塞林格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一經出版便迅速獲得成功,突如其來的關注使本就避世的塞林格更加想要逃避,索性在鄉下買了90多英畝土地,建起小屋,過起了隱居生活。於是,塞林格把自己活成了一個謎。鮮少出現在世人面前,鮮少發表作品,他用迴避的方式代替憤怒和攻擊,他筆下曾經得到許多共鳴的人物霍爾頓被塵封在心底。
塞林格有過兩段婚姻,但好像都並不是那麼幸福。2000年,塞林格的女兒瑪格麗特·塞林格出版了《夢的守望者:一本回憶錄》一書。書中講述了許多塞林格奇怪的行為,以及對於母親強大的控制欲。有評論說這是因為塞林格參加過二戰,有創傷後精神緊張性障礙,但他的女兒又說,對於從軍生涯,塞林格表現出的都是自豪和驕傲。
2010年,塞林格逝世,享年91歲,他帶著生前的一切告別了這個世界,留給後人的是無解之謎。
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麼

每年諾貝爾文學獎即將頒發的時候,人們都為村上春樹操碎了心,就像前幾年,一直在為小李惦記著奧斯卡獎一樣。不同的是,奧斯卡頒獎現場,我們能看到小李迫切的眼神,但是,在諾貝爾文學獎宣布那一刻,村上春樹的表情我們永遠都看不到。
村上春樹說,「最重要的是讀者,獲不獲獎是次要的。」他幾十年如一日,嚴於律己,早起,跑步,規律性地寫作,保證著自己作品的質量和數量。有創作心得的人都懂得,長期從事文字創作的人,到最後拼的都是體力。
《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麼》並不是村上春樹最為人所知的作品,只是藉由自己跑步的經歷而寫就的一些隨筆,是一個孤獨的男人二十年間的歲月感悟。
跑步不是一件難事,堅持跑步也不是一件太難的事,堅持跑一輩子就是一件太難的事,這裡面有太多的自律、控制,把自己的身體規束成一台機器,然後再創造奇蹟。這種狠勁,一般人做不到,村上春樹卻將這變成一種習慣。
圍繞村上春樹的話題很多,諾貝爾文學獎的長期陪跑,還有對於中國讀者而言的翻譯問題,到底誰的翻譯更好。讀書終究是一種個人體驗,每個人的領受都不盡相同,也沒必要求同,如果一位作家能為一位讀者帶來一些前所未有的體會,那對於這兩者而言都是一種幸事。基於此,村上春樹和他的讀者都是幸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