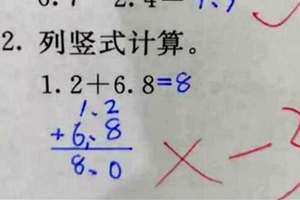連續夭折了兩個孩子,四川南充人何某相信,“八字大、命硬,要撿個孩子來養才養得活、鎮得住命。”
1992年6月,何某來到重慶,揣著一張假身份證,在渝中區南紀門勞務市場找到一份保姆的工作。沒幾天,她把主人家1歲多的兒子從解放碑附近拐走,給這個兒子沿用自己死去孩子的生日、姓名,在南充把這個兒子養大。一晃26年過去了,兒子27歲了,沒人來找過何某。現在,何某突然跳出來,說要給兒子找到親生父母,給自己贖罪。
2018年1月11日、14日,慢新聞—重慶晚報對此事做了連續獨家報道。最近幾天,事件有了重大進展。
2月6日,被保姆何某拐走的兒子劉金心,與丟了兒子的媽媽王小琴(化名),終於在26年之後見面了。
母子團聚,這件事情卻沒有完:在兒子被保姆拐走三年半之後,王小琴是從河南找到了“親生兒子”的,還有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給她出具的《親子關係鑒定》。現在,突然告訴她當年的鑒定報告出了錯、她養了22年的“親生兒子”不是她的,那這個兒子又是誰的兒子?他的親生父母又在哪裡?

劉金心與王小琴終於在26年後見面了
兒子找到了親生母親
就在1月11日,慢新聞刊發《拐走主人兒子當親生養了26年保姆贖罪:找到他親生父母,我就去坐牢》一文當晚,上游慢新聞—重慶晚報記者接到一條線索。
重慶市民何女士來電:“我知道一個案子跟你們這次的報道太像了。26年前,解放碑附近一戶人家,女主人是醫院的,男主人是部隊的,他們家也有一個兒子,1歲多被保姆拐走,保姆也是男主人在南紀門勞務市場找來的,當時保姆持一張假身份證,這戶人家也有一個外婆住在一條街之外。丟了孩子,媽媽每天哭,好慘。”
連夜,上游慢新聞—重慶晚報記者根據線索人提供的地址找到那位外婆的家,又通過外婆聯繫到她的女兒,也就是當年丟了兒子的王小琴。
1月13日,上游慢新聞—重慶晚報記者將這一線索提供給重慶警方。
當日,保姆何某接受重慶警方調查。晚上,何某告訴記者,重慶警方給她做了筆錄、采了血,將她送回南充,並向南充警方調取了“兒子”劉金心的血樣。
王小琴說,1月中旬,重慶警方分別采了她和周文斌(化名,王小琴前夫)的血樣;2月5日,重慶警方給她看了三份《鑒定文書》,並通知她次日與劉金心見面。“這三份報告可以證明,劉金心是我和周文斌的親生兒子。”
劉金心說,2月5日,南充警方去找他,跟他說,親子鑒定報告出來了——王小琴就是他的親生母親。次日,南充警方將他送到重慶。
何某說,她也是差不多同一時間接到了重慶警方的電話,說劉金心的親生媽媽找到了,是王小琴。
2月6日,王小琴在重慶市公安局渝中區分局第一次見到了劉金心本人。幾天前,他們已經通過網路視頻見過彼此的影像。
2月7日,在外婆家,記者見到了王小琴、劉金心母子團聚,外婆、劉金心祖孫團聚的情景。周文斌在外地沒有回來,他們父子暫時沒有見面,周文斌也沒有接受採訪。同時,記者看到了三份《鑒定文書》的複印件,王小琴說,原件在警方那裡。該文書由重慶市公安局物證鑒定中心出具,上面是這樣寫的:“按行標GA/T383-2014、GA/T965-2011進行檢驗”,何某與劉金心“親權關係不成立”,劉金心與周文斌、王小琴“符合雙親遺傳關係”。

王小琴緊握著兒子劉金心的手
曾在河南找到個“親生兒子”
被拐走的兒子找到親生媽媽,從親子的角度講,這件事就划上了句號。但這卻是另一個懸疑的開始——前文提到的重慶市民何女士在爆料時告訴記者:“26年前這個案子,那個媽媽後來找到了兒子,但是,跟你們這回報道的新聞又有許多細節對得上,怎麼會這麼巧合?”
當晚,記者找到王小琴的母親時,她也說,“當年確實女兒在醫院、女婿在部隊,我每天下午要去給孩子送牛奶,保姆也是在南紀門勞務市場找到的,她用的假身份證。但是我們的孩子後來找到了。”
王小琴則一直拒絕接受採訪。
直到1月16日晚,王小琴才同意跟記者見面。她說,1991年3月7日(農曆元月二十一)兒子出生;1992年6月3日,周文斌將何某請到家裡做保姆;6月10日,何某就將1歲3個月的兒子從家中拐走。他們報警、找遍了全國各地,沒有找到。
直到事發後三年半,也就是1995年12月,她和周文斌在河南找到了“親生兒子”,她給記者看了一份收據,上面寫著:“今收到周文斌交來親子鑒定費1500元”,紅章上刻著:“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財務專用”;還有一份由該法院出具的《親子關係鑒定》複印件,原件已丟失,上面寫著:“豫法醫鑒字第19號”,周鵬鵬(化名)與王小琴、周文斌“三者的DNA指紋圖譜符合孟德爾遺傳規律”、“具有生物學親子關係”,蓋的是“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法醫技術鑒定專用章”。
王小琴回憶得到這份《親子關係鑒定》的過程:
“1995年12月,我和周文斌聽說河南省的蘭考縣公安局打拐救了十多個小孩,其中有一個叫周鵬鵬的跟我的兒子很像,正在生病,當地警方已經將他送到開封市的一家醫院住院。可是我們見到周鵬鵬,覺得周鵬鵬跟我們丟失的兒子有的地方像、有的地方又不像,加上事隔三年半,孩子也長大了,我們無法辨認,就提出做親子鑒定。
在醫院,醫生當著我們、警方的面給周鵬鵬采血,密封完整,交給我們。當時可以做親子鑒定的機構不多,整個河南只有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可以做,我們帶著周鵬鵬的血樣來到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法院接收了周鵬鵬的血樣,又給我和周文斌采血,然後我們回重慶,周鵬鵬留在河南。
大概等待了一個月,法院來電話通知我們出結果了,周鵬鵬是我們的親生兒子,我們才去河南把兒子接回來,同時拿到了這份《親子關係鑒定》。”
錯認的兒子哪裡尋親?
可是,重慶警方在2018年出具的《鑒定文書》又明確寫著:周文斌與周鵬鵬“親權關係不成立”。
“周鵬鵬我當親生兒子養了22年,現在告訴我,當年的親子鑒定報告錯了?這太荒唐了。”王小琴說。
那麼王小琴錯認了22年的“親生兒子”又是誰的兒子?他的親生媽媽又在哪裡?如果他知道了,他也要去尋親嗎?去哪裡尋找?
周鵬鵬至今不知道此事,他在外地工作,沒有看到新聞報道,王小琴也沒有告訴他。王小琴編了個理由,周鵬鵬最近回重慶采了血。
王小琴同意報道此事,但希望記者不要採訪周鵬鵬。“我會慢慢告訴他的,但我不希望別人去打擾他。”
王小琴考慮申請賠償
王小琴說,過了年,她要考慮向當年做親子鑒定的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國家賠償,“對我和周文斌,還有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的傷害太大了。爺爺和外公到去世也沒有見到親生孫子,奶奶身體不好,至今不敢告訴她。”
重慶百君律師事務所黃自強律師認為:“根據《國家賠償法》的規定,國家賠償主要適用於對人身和財產造成了直接侵害的案件,比如錯判入獄、錯誤凍結財產等等,但本案是法院內設鑒定機構出具了一份錯誤的親子鑒定報告,應該不在國家賠償的範圍內,也沒有先例。”
“但本案當事人與法院之間有一份收據,當年親子鑒定,當事人是付費了的,雙方就形成了合同關係,這份收據就是合同關係的證明。那麼,我認為當事人可以向法院提出賠償損失,要求賠償多年撫養兒子所支付的費用。根據《民法總則》的規定,民事案件的訴訟時效從當事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之日起計算,時效三年。”
保姆會受到法律懲罰嗎
保姆何某至今沒有跟王小琴見面,她在等待法律結果。她曾說,“我是不怕坐牢的,該我贖罪。”
但劉金心說,“我不想我媽出事,如果她坐牢,我寧願不認親生母親,可是兩邊都是媽媽……”
王小琴說,“我們不再追究何某的責任,為了兒子著想,因為二十多年來兒子一直把她當親生媽媽。我跟警方也是這麼說的,我不追究了。”
重慶百君律師事務所黃自強律師說:“這是公訴案件,是不以當事人意見為轉移的,但受害人表示諒解不予追究,司法機關可以作為情節考慮,比如對嫌疑人從輕處理、判處緩刑等等。”
“但最後到底怎麼判,還是我上次說的時效問題,1992年的拐騙兒童案,適用1979年的《刑法》,判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最高刑不滿5年的,追訴時效是5年;如果20年以後必須追訴的,比如社會影響非常惡劣、社會傷痛無法消除的,需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但是,如果犯罪行為有連續或者繼續狀態的,犯罪行為從行為終了之日計算,但何時是行為終了之日,存在爭議。”

1月12日重慶晚報報道
1月11日慢新聞報APP道:
拐走主人兒子當親生養了26年
保姆贖罪:找到他親生父母,我就去坐牢
48歲的何某無意中看了一檔電視節目——《寶貝回家》,講的是一位七八十歲的老母親,一輩子都在找四五十年前丟失的孩子,滿頭白髮了還在找。這勾起了何某26年前的一件往事。
上周,何某輾轉聯繫到慢新聞—重慶晚報記者,她說:“我一定要把這件壞事說出來,說出來,我才能贖罪。”
保姆
1992年,22歲的何某在重慶解放碑附近一戶人家做保姆,主人家有個1歲多的男孩兒。只做了兩三天,她就把這個男孩兒拐跑了。
應該是五六月份,何某記得剛栽完秧子,她從四川省南充市李渡鎮五大山村(原)來到重慶,揣著一張撿來的身份證,來到儲奇門人才市場。她打定主意,要用這張身份證找一個保姆的活路。
她站在儲奇門人才市場等機會,等來一個男人。男人問她做不做保姆,她說做。男人問她要身份證,她就把那張撿來的身份證給了男人。她跟身份證上的人還真有幾分相像,男人沒有仔細辨認,也是為了省5元錢的登記費,便私自把她帶回家。
家裡有個小男孩兒,在地上走得歪歪撇撇,看起來一歲零四五個月的樣子,何某去抱他他也不認生。
兩三天之後的一個早上,女主人給孩子餵過早飯,把孩子交給何某,出門上班,隨後男主人也出門上班。何某就抱著孩子出門了。碰到隔壁老頭兒,問“你上街買菜呢”,何某應了一聲“哦”,抱著孩子來到菜園壩汽車站,坐上一輛大巴車回了南充。途中路過合川,她還買了一碗稀飯喂孩子,孩子不哭也不鬧,一路順利。
何某就在南充把這個拐來的男孩兒養大,一晃男孩兒27歲了,沒人找過她。
鎮命
何某18歲結婚,19歲有了頭一個孩子,是個男孩兒,冬月里生的,四十多天之後,深更半夜死了,抱到河邊挖個坑埋了。
21歲,何某有了第二個孩子,也是個男孩兒,臘月里生的,十個多月之後,也是深更半夜,又死了。何某回憶,當天吃了晚飯,孩子哭鬧不止,哭到半夜不哭了。她想起第一個孩子也是這麼死的,生怕這個也死了,慌忙抱到鎮上醫院,醫生說已經死了。她抱著死去的孩子往家走,她不能讓村裡人知道她又死了個孩子——死一個死二個要遭人笑話的。她敲開村裡的獨身啞巴的門,給了啞巴10塊錢,連夜到河邊挖個坑把孩子埋了。
埋了孩子第二天,她就去找丈夫。她丈夫在外打工,村裡人都以為她是帶著孩子去的,又死了孩子這件事就沒有人知道了。那個年代,村裡人都顧著吃飽飯,也沒有人真的在意。
死第一個孩子的時候,村裡的老人就警告何某,“你八字大,命硬”,“要撿個孩子回來養才養得活、鎮得住命”。何小平這回信了。
死了的孩子沒有銷戶,她把拐來的孩子當親生的養,沿用了第二個孩子的戶口、生日、姓名,叫劉金心。那個時候,何某沒有意識到她是拐走了別人的孩子,她覺得“我沒了孩子,這個孩子跟我死了的孩子一般大,就像是我的”。
這個孩子似乎真的為何某“鎮住了命”,以為自己不會再有生養的何某,在1995年又生了個女兒。
親生
生下女兒之後,何某第一次想到“把拐來的孩子還回去”,但是她很害怕,怕坐牢,男孩兒就一直養在何某身邊。
丈夫劉小強(化名)不喜歡這個男孩兒,何某堅持“你不喜歡就算了,反正我要這個孩子”。夫婦倆常常因此吵架,劉小強常年不回家。
何某一人帶著兩個孩子在李渡鎮租房子、打零工,飯館、茶館、工廠,見活兒就干。2000年,她攢下2萬5千元錢,那時南充市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要5萬元,隔著一條街就是孔邇街小學。為了方便劉金心讀書,她把2萬5千元全部拿出來付了首付。她每天帶著小女兒出去打工,出門之前把飯做好,掛一把鑰匙在劉金心的脖子上,劉金心放了學自己回來吃飯。
2003年,何某和劉小強離婚。
離婚後的何某做了兩筆“大生意”,她跟一個親戚去黑龍江販衛生筷回南充賣,50元一箱買進,75元賣出。南充市的大小飯館都被她跑遍了,一年賺了七八萬。後來生產衛生筷的廠子因不符合國家標準倒閉了,何某回到飯館端盤子。
前幾年,何某又去山西販煤炭回南充賣,夏天一噸煤進價600元,她賣1200元,冬天一噸煤進價1000元,她還賣1200,兩年賺了十五六萬。
2014年,何某用這筆錢又在南充市買了一套房子,三室一廳,90多平方米,單價4500元,首付13萬,貸款20年,寫的是劉金心的名字。
除了何某和前夫劉小強,沒有人知道劉金心是拐來的,鄰居只看到何某不容易,“一個人把兩個孩子拉扯大”,劉小強也承認,“我沒怎麼管兩個孩子,都是她在操心,新房子是她買給兒子結婚用的。”後來劉金心和女朋友分手了,據何某說,是因為訂婚的時候女方要6萬元彩禮單,但她只拿得出2萬元。
慢新聞—重慶晚報記者在裡屋看到一套護膚品,何某說是去年9月份劉金心送給她的生日禮物,劉金心也在電話里證實,“因為我媽一輩子不容易,捨不得吃捨不得穿,我每個月給她一兩千塊錢喊她喜歡什麼自己買,但她都替我把錢攢下來,所以我現在就看她差什麼買給她。”
何某說這些,是要反覆證明,“我知道我自己做了歹事,可是我一直把兒子當親生的養,兒子也把我當親媽。”
尋親
這些年,何某無數次想過要給這個拐來的兒子找到親生父母,“那時候我太年輕,不懂事,死了兩個孩子就像得了失心瘋。後來我自己有了生養,體會到當媽的心,丟了孩子心裡該有好痛。”可是“一想到要伏法,我就不敢了”,哪怕三四年前,前夫劉小強跟她發生口角後,揚言要舉報她,“敲詐”她13萬元,她也認了,寫下一張欠條。不過劉小強說:“那是我一時意氣,我知道那是何某的死穴,嚇唬她的,欠條過後被我撕了。”他強調,“拐個孩子,是她自己的主意,我是不同意的,不過她這些年一直對孩子很好,我基本沒怎麼管。”
何某去廟裡求了一尊觀音菩薩,把菩薩帶回家擺在客廳最顯眼的位置,“我把我做的歹事全部說給菩薩聽,求菩薩原諒我”。接著她一個人偷偷來了一趟重慶,那是她時隔多年再次來重慶,她想找到當年那戶人家,可是“一切都變了樣,翻天覆地,全是高樓大廈,我找不到路”,何某隻好又回去。
直到2017年夏天,何某無意中看到一檔電視節目《寶貝回家》,“七八十歲的老母親,一輩子都在找四五十年前丟失的孩子,滿頭白髮了還在找。我覺得我自己不是人,作孽呀。”
何某跟兒子、女兒坦白了,女兒哭著求她,“媽媽不要去自首,我怕你要坐牢。”但何某執意去了南充市公安局順慶區分局打拐辦自首。
2018年1月3日,慢新聞—重慶晚報記者也去了南充市公安局順慶區分局打拐辦。警方證實:大約半年前採集了何某、劉小強、劉金心的DNA,可以證明的是劉金心與何某和劉小強沒有血緣關係。
劉金心不能接受,“那天我買了一瓶白酒,把自己灌醉了。”後來他離開南充,去了廣州一家電子廠打工,月薪5000元,“我前幾天又把自己喝進了醫院,心裡憋得難受。”但他寧願憋著也不願多談,只說,“我媽對我這麼好,我沒想過我媽不是我媽,親生的能找到就找,不能找到就算了。”
劉金心初中輟學,是何某覺得最對不起他的地方,“如果他跟著他的親生父母,在解放碑長大,也許會讀大學、碩士、博士,一定會有出息。但他跟著我,吃了很多苦,書沒讀好,也沒個好工作。”
劉金心的DNA被放入中國失蹤人口檔案庫,可是,半年過去了,通過比對認親沒有找到他的親生父母。
尋親關鍵詞:解放碑、大院、醫院、綠色大門、夢生……
何某很著急,上周,她再次來到重慶,希望通過慢新聞—重慶晚報公開尋找劉金心的親生父母。
線索一:解放碑
何某說,1992年來重慶,她先在臨江門舅舅家住了一晚,是舅舅給了她那張撿來的身份證,還給她出了做保姆拐孩子的主意。但舅舅十多年前去世之後,她跟舅舅一家就失去了聯繫,也忘了他家的具體地址。
從舅舅家走到解放碑2路車總站,何某一路打聽,走到儲奇門人才市場,遇見男主人,男主人帶著她從儲奇門人才市場出來,坐了一趟公交車,大約兩三站就到了,好像又回到了解放碑。
當年的2路車總站,至今仍在解放碑鄒容支路。1月4日,慢新聞—重慶晚報記者帶著何某從鄒容支路出發,走到儲奇門人才市場,試圖幫助她尋找記憶,但她說,“記不住了,都變了。”
而就在十幾天前,儲奇門人才市場也被拆掉,勞動力卻沒有散去,他們還在原地站著等待,幾十年了他們習慣在這裡尋找僱主。一直生活在附近的陳婆婆說,往前走就是凱旋路、較場口、解放碑一帶,不需要坐車,幾十年來也沒有公交車;凱旋路倒是有公交車去七星崗、文化宮方向,原來是9路,現在是109路。她當年會不會是走到凱旋路,又坐的車?
南充警方也來重慶找過。原解放碑派出所、較場口派出所、大陽溝派出所整合為新的大陽溝派出所,但是南充警方沒有在大陽溝派出所找到當年的報警記錄。
線索二:成片的大院子、醫院
何某說,男主人帶她回家,是一個大院子,高高的門檻,裡面住了很多戶人家。雇她的那戶人家好像是院門正對著的那間,屋裡搭了閣樓,一家三口睡在閣樓上面,女主人好像是醫生或者護士,曾經說過一句“我們醫院忙得很”。何某還記得那一片好像有成片的大院子。
根據老重慶人回憶,1992年有成片大院子的,很有可能是七星崗。
慢新聞—重慶晚報記者找到七星崗街道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服務中心,見到66歲的文正光,他從1957年就住在七星崗一帶,退休後返聘負責退休人員管理工作。他回憶,現在的財信渝中城,就是當年的上三八街5號,這個地址有9個大院子連成一片,從上三八街5號附1號到附9號,旁邊是七星崗公社醫院,如果有醫生或者護士住在這裡,那就對了。
文正光又發動了發小群一起尋找,大家七嘴八舌,其中有個老居民說,依稀記得附8號院,院門正對著的一戶人家,女主人是護士,聽說她後來去了上海,早已失去聯繫。但沒人記得大院兒曾經有人丟過孩子。
慢新聞—重慶晚報記者找到當年管戶籍的老片警楊林,他說:1992年丟了一個孩子,這麼大的事,除非沒有報警,如果報了警我肯定知道,但我記憶里沒有接到這樣的案件。
線索三:綠色大門
何某又說,她記得院子大門刷了綠色的油漆。
挨著上三八街5號院的,是工讀院,當年這個院子的大門還真刷了綠色的油漆。我們找到一位老居民,54歲的蔣曉玲,她說,院子里有一戶人家,也是1991年生了個兒子,年份對得上,但沒聽說過丟孩子的事,後來搬走了,也就沒有聯繫,偶爾在街上遇見過一兩回,也沒有留電話。
線索四:“夢生”
何某說,白天男女主人出門上班,她一個人帶孩子,到了下午五六點鐘,會來一個老太太,給孩子喂飯,喂完飯就走,應該是孩子的外婆。她曾經聽過外婆喚“夢生(音)吃飯了”,夢生應該就是孩子的乳名。
外婆帶何某認過門,外婆家跟大院子就隔著一條街,是一棟兩層樓的樓房,外婆住二樓,她的那間屋子可以望到江。
文正光說,從前,與上三八街5號院、工讀院隔著一條街,確實有一棟兩層樓的紅磚樓房,當年沒有高樓大廈的遮擋是可以望到江的。但是有沒有住著那樣一位外婆,就不知道了。
坐牢未必能如她所願
法律之外她該如何贖罪
何某也不知道,我們尋找的路徑是否正確,“如果地址是對的,那戶人家丟了孩子為什麼不報警?或者,地址找錯了?也許我把孩子拐跑之後,那個家庭就破裂了,兩口子離了婚,又各自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不方便出來相認了?”她有很多猜測,“我只想找到孩子的親生父母,找到了我就去坐牢,給自己贖罪。丟了孩子的媽媽,一定一輩子都在找這個孩子,是我害了她。”
可是,南充警方說目前證據太為單一,無法證明何某當年拐騙了一個孩子。前夫、女兒、鄰居都說何某精神狀態正常,劉金心認為“媽媽不可能在我的身世問題上開玩笑”,慢新聞—重慶晚報記者與何某溝通後也判斷她精神正常、邏輯清晰。
重慶百君律師事務所的黃自強律師說:“我國《刑法》在1997年做過一次修改,1997年以前,用的是1979年制定的《刑法》。根據從舊從輕的原則,1992年的案子,應該按舊法判。”
“根據1979年《刑法》,拐騙,判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1979年《刑法》還有一個關於追訴時效的規定:最高刑不滿5年的,追訴時效是5年;刑期5年以上不滿10年的,追訴時效是10年;刑期10年以上的,追訴時效是15年;無期徒刑和死刑的,追訴時效是20年;如果20年以後必須追訴的,比如社會影響非常惡劣、社會傷痛無法消除的,需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只有在對嫌疑人採取了強制措施以後,嫌疑人逃避偵查的,才不受追訴時效的限制。”
“但是,如果犯罪行為有連續或者繼續狀態的,犯罪行為從行為終了之日計算。但何時是行為終了之日,這就存在爭議了。另外,拐騙兒童罪是指以欺騙、誘惑等手段使不滿14周歲的男、女兒童脫離家庭或者監護人的行為;可是,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嫌疑人把兒童拐騙之後怎麼辦,一方面她把孩子當親生的養大,另一方面她對親生父母造成的傷害無法彌補。以上只是我從法律層面的分析,最後怎麼判,由司法機關做更多調查才能下結論。”
“從目前的案情來看,沒有找到受害人,案子的推進會有一些重大障礙,需要進一步收集和固定證據,當事人想坐牢,恐怕未必能如她所願。”
何某聽了不知是喜是悲,她說,“那我怎麼才能贖罪呢?我說給菩薩聽,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