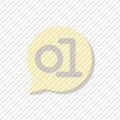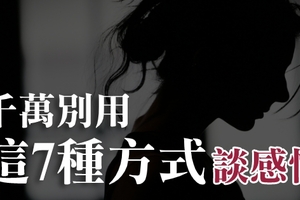①
2018年1月21號,許承安結婚了。
婚禮是在教堂舉行的。那個我小時候特別喜歡的,長大後依然幻想著要在那裡和許承安交換戒指的教堂。
客人不多,除去新郎新娘雙方的家人和親戚,剩下的外人只有我和伴郎兩人。
許承安一身黑色燕尾服,站在主婚人面前,一手與新娘十指緊扣,一手握著話筒對下面的親戚好友說:「婚禮從簡,這是我們倆共同的意思。」說到這,他側臉看了一眼身旁的新娘,接著繼續說:「請的人不多,但能得到你們的祝福,我們深感榮幸。」
在一片掌聲中,許承安轉身與新娘面對面,然後掀起她頭上的白紗,與其深情相吻。
新娘我並不熟悉。現在僅是第一次見面。但站在客觀的立場上看,不得不承認她是一位好姑娘。
從早晨化妝,拜別父母,坐車到禮堂,全程下來她都面帶微笑。那種淺淺的,帶著春風般沁人心脾的笑容。惟有在給自家父母下跪告別時,她才眼角現淚。但這更給人一種梨花帶淚的感覺。恨不得馬上張開臂膀擁她入懷。
在宴席上,她表現得更是落落大方,舉止從容得體。每桌客人都輪流敬完酒後,她特地吩咐酒店的服務員為親戚朋友們備好她和許承安提前準備的禮物,還不忘提醒她們在酒席結束後為好友們奉上茶水。
事無巨細,周到體貼。這是這位新娘子留給我的第一印象。如此溫婉可人,又觀察入微,善解人意,若是換作我是許承安,也定會對這樣的女子傾心傾愛。
如此郎才女貌,天作之合,想必他們往後的日子應該會其樂融融,幸福溫馨。
身為許承安的哥們,兼這場婚禮的伴娘,我比在場的任何一個人都更熱切地希望許承安能幸福。
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他幸福,只是想到這幸福不是因為我,多少還是會有些難過。
②
我和許承安的哥們情誼,要追溯到很多年前。
那時候我們都還是情竇未開,對很多事情都沒有太多想法的年輕人。不在意別人的看法和言語,不在乎那些無關緊要的人與事。
用一句很文藝的話來說便是: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
因此,每天下午放學後,我們都還是會一如從前那般勾肩搭背地走在回家的路上。甚至很多時候,我吃過的冰棍,喝過的礦泉水,啃過的蘋果,許承安都會從我手中或嘴中搶去,爾後若無其事地吃起來。
當然,偶爾的,我亦會如此。
許承安也特別仗義。每次他家裡有什麼好吃的,他都會塞進書包帶到學校給我。儘管我們同校不同班,他在理科班,我在文科班。但這一點都不妨礙我們哥們友情的發展。
平日里,除去上課時間,其餘的個人時間,我們都會廝混在一起。周末不上課了,就出去爬山或者什麼事也不幹,就沿著學校附近的一條人行道從正午走到黃昏。
偶爾的,當手頭寬裕,兜里有零錢時,我們還會在晚上去學校附近的一家電影院看電影。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過的女孩》就是在高中時,我和許承安一起看過的。事隔經年,如今許承安已成家立業,而我依然孤身一人,但電影里的情節和人物,我還依稀記得很清楚。
想想高中三年,最開心的不是後來我們都如願看考上了自己喜歡的大學,而是在那段自覺最孤苦彷徨的歲月里,身邊始終有一個與你並肩同行,風雨同舟的人。
那個人,就是許承安。
③
當我真正意識到自己對許承安的感情時,我和他,我們兩人已分散在不同且相距甚遠的兩座城市。
他在北京,我在浙江。
浙江到北京,全程一千三百多公里。這個距離,阻斷了我們之間在高中時期慣有的見面機會,卻萌發了另一種意味不明的情愫。
當清醒感知到這種情愫的存在時,它已然存在許久了,只是我本人未曾察覺,而許承安那個遠在千里之外的人,亦無從得知。
我們依然一周一次電話,一月一封信,或者一學期回家聚一次。即使分離兩地,我們仍然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並且,這種關係在一定距離的相隔之下,變得愈發醇厚,就像陳年佳釀,歷久彌香。
直到在大三的下學期,身邊一位朋友向我表白,而我又以「我有男朋友」這個理由拒絕掉他。那時候我才意識到,隔著千山萬水,萬一許承安被別人拐走,或者他拐了別人,那我怎麼辦?
拒絕掉林陌成的當天晚上,我就給許承安打電話。他很詫異,因為離我們每周約定好的時間還有兩天,而我卻提前給他打了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