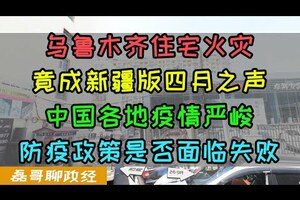摘要:畢竟她還是個孩子,為什麼她竟然可以隨意地在世界版圖上移動,而我們卻都被困在這裡。
在我還沒見過小元之前,便聽說了她許多事情,那是很多年前,七年,八年。那會兒,我們的朋友大雄沉浸在對她單方面的熱戀中,在多次集體大醉的排檔上,他說起小元,甚至為她寫了一本書。這本書在前年無聲無息地出版了,我沒有買,我想其他人應該也是。一方面是因為他才華的有限性顯而易見,另一方面,二十七歲新年過後我便去了北京,漸漸和他們所有人斷了聯絡,他們彼此之間應該也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沒有如期望中那樣,成為什麼真正出色的人。大部分人遵循規矩,混得不錯,但是與出色絕對不沾邊。但是我們並不愚蠢,紛紛接受了自己作為平庸小人物的存在,沒有苟延殘喘,也沒有滯留在任何灰色地帶。大雄是個典型人物,當他把有限的才華投入電視劇本的撰寫時,賺到很多錢。
我一度懷疑小元是被杜撰出來的,因為她被描述得像個夢。哦,或者說,更像是一個理想,一個不管是誰都想要成為的人。那會兒她十七歲,高中時作為交換生去了荷蘭,之後依然是以交換生的身份去了法國和西班牙,通曉英文和法文,能用西班牙語做日常對話。她的語言天賦有賴於超群的智力和記憶力,因此只要她願意,她幾乎可以在任何有望改變人類現狀的領域有所建樹,但是她偏愛文學,試圖與普通人一樣從悲傷的文字中尋得意義。高中畢業以後她回國念大學,浙江大學中文系。完全是一種浪費,哪怕念哲學都對她的頭腦更有益,天賦異稟的人卻最不把才華當回事。這給了大雄不切實際的希望。那段時間他頻繁往返於杭州和上海,包里裝著博爾赫斯的小說和卡瓦菲斯的詩集。我敢說,不管是他還是小元對於這兩個人都從未產生過真正的興趣。
但是小元在一個學期後便退學了。大雄認為她是出於對規則的挑釁以及少年心氣,但當我認識小元以後,便覺得這樣的決定多半是出於對整部人生過早的洞察,接下來她對外部世界的拋棄也變得更加直接。
之後大雄提起過她兩次,一次說她去非洲參加了一個人道主義援救項目,一次說她在大西洋的船上採集標本,三個月後上岸。很難說這裡面是否有杜撰的成分,他對她的描述一定有主觀臆斷,然而小元的經歷又在大雄以及我們所有人的經驗之外,他不可能憑空捏造出一個非洲人道主義項目,我懷疑他對非洲的全部認識來自於海明威描寫的乞力馬扎羅山。所以他應該只是省略了一些部分。為什麼她可以那麼瀟洒。實際點來說,她是如何賺錢的,如何解決生計問題。畢竟她還是個孩子,為什麼她竟然可以隨意地在世界版圖上移動,而我們卻都被困在這裡。
直到他們分手,我們才終於感覺鬆了口氣,世界的齒輪彷彿終於卡對了地方,不會再發出刺耳的聲響。
「她啊,真是一個流浪兒。」我們勸慰他。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她就是那種人,浪子。你比我們更明白。」
「你們怎麼會這麼想。」他幾乎倒退了一步,露出非常吃驚的表情,繼而是冷冷的嫌惡。
大雄最後一次找我,我已經在北京住了兩年。他在電話里說小元申請了美國的學校,要從武漢到北京來辦簽證,想要找個落腳的地方。幾天,最多一個星期就夠了。問題在於,那段時間我的狀況非常不好,租住的房間很小,三十平米的一間被房東用一排柜子割出客廳來。窗戶底下便是垃圾場,終日無法開窗。四周偏僻,荒涼。而且我正在交往一個男朋友,為了維持這段事後想起來糟糕透頂的關係,我幾乎每晚都去他家過夜,完全沒有意識到我們的關係瀕臨結束,無可挽救。但是我除了一張靠牆的小床外,確實還多出一張沙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