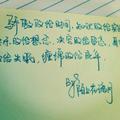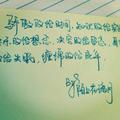一
父親從家鄉打來電話問我:「你公司里還招不招清潔工什麼的,你看我去行不?你也好有個照應……」我立馬打消他的念頭,堅決地告訴他:「人家不要五十歲以上的!再說人家早招完了,不缺人!」父親這才黯然地掛上電話。
都怪我多嘴,前不久和母親打電話時說起過,公司有不少老頭老太太來應聘清潔工。誰知道這無意中的閑聊竟傳到父親耳朵,讓他萌生了要來應聘的願望。虧他想得出這主意,我可丟不起這人。再說,我當初來北京就是為了離父親遠遠的,省得他整天看我不順眼。
但是沒想到這段不愉快的談話竟成了我和父親的最後一次交流,還沒出半個月,我突然接到母親的電話,她忍住悲痛用盡量平靜的聲音告訴我:「孩子,你回來趟吧,你爸他……沒了。」
我連夜坐在回家鄉的火車上,一路上耳朵里滿是火車哐哐的聲音,震得人心裡發緊。這個方向是這麼多年我一直抗拒的,我曾一遍一遍背離這個方向走遠,只是因為不想原諒父親。
二
我和父親的感情一直不好,相比妹妹的乖巧,從小就調皮的我總是不被父親喜歡。沒有什麼文化的他處理問題的方式總是簡單而粗魯,童年的時候,挨父親的打罵對我來說早已是家常便飯。
小時候,我偷偷拿了母親放在桌上的五毛錢買糖吃,父親知道後氣得不得了,把我摁在炕頭,操起手裡的皮帶就往我身上抽,邊打邊不解恨地罵:「老子怎麼養了你這麼個不爭氣的東西,我看你以後還敢不敢再偷了!」又寬又厚的皮帶打在身上是無法忍受的疼,母親在一旁心疼得直流眼淚,拉著我喊:「孩子,快和你爸認個錯!」可那時的我只是用牙緊緊咬住嘴唇不吭一聲。
初中畢業後,我沒有考上重點高中,便自作主張報了一所職業學校,我想反正自己又不是父親心中的那隻「鳳凰」,又何必浪費家裡的錢去看父親的臉色,還不如早早地去掙錢離開這個家。
在那所校風很差的學校里,女孩子平時大多把時間浪費再穿衣打扮上,我也沒能倖免。第一次從學校回家時,我頂著一頭自以為很時尚的黃頭髮,沒進家門,隔著老遠就看見父親氣洶洶地朝我走過來,不顧我的反抗和叫喊,一下子把我拎起來拽回家。他指著鏡子里「濃妝艷抹」的我破口大罵:「你看看你現在是個什麼鬼樣子,學生家不好好念書,整天都想些什麼!」我在心裡冷笑,心想這還不是拜你所賜,你也就打罵我的時候能想起我,這樣想著臉上便露出不屑的表情。父親見我不知悔改的樣子,氣得抓起桌子上的手電筒,朝著我的膝蓋就不知輕重地砸了下來。我看著慢慢腫起來的膝蓋,好像這一塊肉不是從父親身上掉下來似的,我的心裡頓時荒涼成一片。也許就是那一刻起,我發誓自己永遠都不會原諒父親。
三
從那以後,即使周末我也住在學校不回家。我拼了命地學習,這是當時我能想到的遠離父親的唯一出路。母親只是隔段時間就把錢送到學校,我們之間的話題也總是繞開父親。母親看著我瘦得不成樣子,心疼得直掉眼淚,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執意不肯回家的我面前放更多的錢,母親說:「孩子,別心疼錢,你爸現在生意還不錯,咱不缺錢。」我聽了,心想總有一天我會掙很多錢,用過父親的錢一分一毛我都會還給他,那個時候,我和父親就兩清了吧。
也許除了我自己,誰都沒有想到在職業學校「混日子」的我也能考上大學。可離家千里,我才真正體會到想家的滋味。宿舍里的姐妹都常常抱著電話和遠方的父母聊天談心,只有我,即使往家打電話,也只是和母親說兩句就掛,我怕父親會突然接過電話,那種沒話找話的氣氛只會讓電話兩端都覺得尷尬。
一年裡只有過春節的時候我才會回家,常常是在家沒住幾天我便又回到學校。多餘的時間我都用來打工,賺來的錢除了交學費,我便一點點攢著,那個「兩清」的誓言我從來沒有忘記。
畢業後,雖然工作和生活困難重重,但我還是說服母親,執意留在了北京。我暗暗發誓,只要這裡有一口飯吃,我就決不回去。
四
只是沒想到就在金融危機肆虐的那個冬天,我也不幸丟掉了工作。我原本打算春節留在北京繼續找工作,可母親卻突然打來電話:「孩子,回家過年吧,你爸說想你了。」我心裡一動,這是我記憶中第一次聽說父親想我。但我猶豫再三還是沒有回去,心想自己這副落魄模樣,回到家還不知道要遭到父親怎樣的責備呢。
除夕夜的前一天晚上,我在租來的小屋裡隱約聽到外面有敲門聲,打開門一看,父親和母親兩人正拎著大包小包在門口站著,我呆在門口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千里迢迢的距離父母怎麼會特意趕來和我過春節?這諾大的北京城他們又是怎樣僅憑著信封上的地址就找到了我?
母親悄悄對我說:「你爸這段時間老念叨著心裡不踏實,非要過來看看。」我扭頭看著正在廚房裡忙活的父親,父親儼然不再是當年那個朝我吹鬍子瞪眼的男人,他佝僂著腰在那裡一下一下略顯吃力地切著菜,嘴裡卻還哼著小曲,我的心裡不知是什麼滋味。
那段時間,我和母親聊天的時候,父親總是假裝咳嗽兩聲,說一句「你們娘兒倆說吧,我出去走走」,可常常看他在旁邊磨蹭了半天,還沒動身出門。
其實那段時間父親的身體就一日不如一日了,只是粗心的我只顧著找工作,卻不知道父親是拖著病體千里迢迢來北京看我。
五
回家後見到母親,母親彷彿一夜之間蒼老了許多,她一遍一遍向我念叨父親臨走前一直不肯合眼,他是在等我回家。
雖然心裡難過,我卻安慰母親:「有我妹送他走,他也算沒什麼遺憾了,反正我爸……也不差我一個。」
聽了我的話,從來沒打過我的母親狠狠地給了我一巴掌,「不差你?孩子,你這話可真傷天理啊!你知道嗎,你爸最疼的人就是你!你上職業學校那幾年,你爸生意一點也不好,家裡日子緊得很,可他每次都讓我多給你帶些錢去,有時候你妹妹幾個月都吃不到一頓肉。孩子,你爸疼著你呢。」
原來在我最恨父親的時候,父親卻還一直想著我。母親告訴我:「你從小就比一般孩子調皮,脾氣又倔,你爸看你不學好心裡著急啊,哪個當爹的不疼自己的孩子?你爸小時候就是太受你爺爺嬌慣,不愛念書,十七歲就出來給人出苦力,你爸是怕你多走彎路啊!」
我默默整理著父親的遺物,在父親抽屜的底層,整整齊齊地放著我大學時曾寫給母親的信,我用顫抖的手捧起貼在臉上,那上面彷彿還有父親的氣息,那嗆人的煙草味,和那濃得化不開的愛,讓我的眼淚忍不住流下來。
從小到大,我一直為父親的簡單粗魯的處事方式感到不屑,原來,在父親粗獷的管教之下是他毫無保留的愛。而我卻從來沒有試圖走近看一看,只顧著自己的感受,任由自己像一隻掙脫了線的風箏,離他越來越遠。可我知道,父親的愛從未離開,只要我轉身,就能緊緊地被它擁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