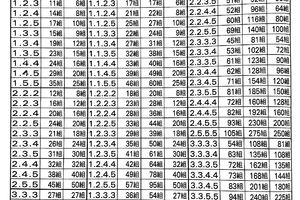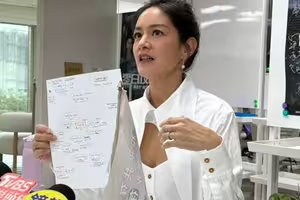[NOWnews今日新聞] 2025年,美國好萊塢,與其餘的世界電影產業都期待2025年是電影的大年。然而,美國通膨、景氣低迷,電影公司縮衣節食,片廠與獨立製片公司紛紛減產是事實。年中仍舊有因罷工而延遲製作的美國電影紛紛完工,蜂擁而入坎城影展。從七月底的景況來看,我們確信四月底湧入坎城的美國好萊塢「大片」,恐怕只有總數的一半;全球電影產業似乎才正要走出「AI」導致的「工會罷工」窘境。
從威尼斯、多倫多影展的片單看來,許多「趕工」中的電影,舉凡盧卡格達戈尼諾(Luca Guadagnino)的「#MeToo」驚悚片《After the Hunt》、沙夫戴兄弟(Safdie Bros.,兩人單飛各有新片!)、凱薩琳畢格羅(Kathryn Bigelow)白宮驚悚片《A House of Dynamite》、尤格藍西莫(Yorgos Lanthimos)的韓國科幻片翻拍《Bugonia》、PTA(保羅湯瑪斯安德森)《一戰再戰》、朴贊郁《No Ohter Choice》、阿薩亞思(Olivier Assayas)的普丁傳《The Wizard of the Kremlin》、保羅索倫提諾(Paolo Sorrentino)《La grazia》、葛斯范桑(Gus Van Sant )《Dead Man's Wire》、戴托羅(Guillermo del Toro)《Frankenstein》,奧斯卡金獎名導聯袂出籠。
還以一些片,傳聞擠不進去坎城窄門:賈木許(Jime Jarmusch)《Father Mother Sister Brother》、舒淇《女孩》、《索爾之子》名導László Nemes《Orphan》...坎城拿不到,坎城不要的,還是本來就去奧斯卡。是是非非,總是野心勃勃的坎城策展人福懋(Thierry Frémaux),貌似今年的成績單,現在才要開始打分。我們相信,他早已盡力,若有勉強趕上秋季,今年急著上映結案的大師傑作,那功過也肯定會記上他成績單一筆。電影的世界當然不是只有這些大師,但影展與電影工業的遊戲便是如此樸實無華。
*
坎城。在國際媒體交流的場合,來自臺灣台北的我貿然冠上外交小尖兵的使命,向每個詢問台灣影壇、政治近況的外國記者介紹台灣處境。移民北歐瑞典的前南斯拉夫出身的記者女士在媒體室外與我一起抽菸,她告訴我曾學過中文的她,十分崇拜我們的蔡前總統的施政。我告訴她,如今同個政黨的男總統,告訴我們應該台灣全國未來,全寄望於一場將要來臨的「大罷免」選舉,以解決「歐洲常見的」國會僵局問題。
於此同時,總統說,我們應該打造與美國同陣線的民主高科技產業鍊,以解決台灣尷尬國際處境;同時間更有民眾喊出「民主影視產業鍊」打擊中國用以「認知作戰」的抖音、小紅書。外國記者表示同情,但世界充滿戰爭,坎城也是政治的舞台,她們真的需要知道台灣如此瑣碎的在地脈絡嗎?僅是因台灣今年交出《左撇子女孩》於坎城亮相,或者因為晶圓半導體工廠,我們是《經濟學人》形容的「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坎城影展剛結束,伊朗導演賈法潘納希拿下金棕櫚,六月我們就看到以色利與伊朗的政治危機,而日前台灣大罷免、剛結束的日本參議院選舉,政治無所不在。但全球電影人仍舊在問:藝術影展選映高級娛樂電影如果被政治佔滿,真的能拯救「人去樓空」的戲院景況嗎?全球都在問,台灣稍微晚一點,上半年戲院不景氣,直到《F1》和《侏羅紀公園》,暑假學生回籠,戲院才稍微喘口氣。
坎城影展頒獎典禮上,台上勞勃狄尼洛被李奧納多迪卡皮歐介紹出場,他激賞法國作為自由民主的市場,反觀美國缺乏政治實踐的能耐。法國「電影筆記」影評人,在坎城影展結束的回顧短文寫道:我們的國家足夠民主嗎?於此同時,法國已經是以最激進的、甚至親中左派政黨能在國會佔有多數的國家。在影展落幕前後,韓國和波蘭,也各自選出了的總理,一左一右,但當地出身的記者都表示無改對國家內部政治意識型態對立,極右派興起的憂心。中國記者明顯士氣低迷,中國低迷景氣、高失業率、《挪吒2》票房新高紀錄假象,憂心忡忡。當時,一部「各方面」破紀錄的作者電影,破慣例的趕在死線截止後多時,闖入為主競賽。
畢贛《狂野時代》能成為民族英雄嗎?時隔坎城兩個月,「A24」破天荒地簽下票房明顯造假的《挪吒2》北美發行。這紙合約,是誰在救誰?在中美關稅貿易戰波及電影業,戰事還沒落幕,我們都在等電影要怎麼回應政治局勢。我有足夠的時間思考這個問題嗎?
或許,其他說「華語」(普通話)的人也都在問這個問題,我們有足夠的時間嗎?當全球反共情緒高漲,台灣國內網路同溫層亡國感精神焦慮強烈,我們仍舊是珍珠奶茶與香蕉的國度,國民忙著日本賞櫻看萬博。彷彿皇民化時代還沒有結束,事實上,我國兩黨對日本殖民主義痕跡的「轉型正義」都仍著墨太少。於此同時,日本「國家隊」是今年亞洲電影於坎城一支獨秀、表現最亮眼的區域,連續第二年,「日本之夜」比下了沒有長片入圍的韓國,與他們知名的「韓國之夜」。同時政府大力支持、剛開始起步的「台灣之夜」、「泰國之夜」、與刻意同天同台競技的「中國」,都還在坎城持續摸索自己的定位。但日本的政治與經濟並不好。這些電影真的能拯救日本影壇嗎?
日前,坎城影展平行單元「影人雙週」放映的《國寶》,以三小時片長,持續霸榜日本院線。

話說回來,坎城影展酒會上大家到底說了什麼?我已然忘記。坎城影展的記者,必須「提前一小時」取消票券的新規定,筆者不得不前往觀賞年度影片西班牙卡塔蘭地區出身導演奧利佛勒賽《穿越地獄之門》(Sirat)。影片一如筆者預期,成為坎城影展年度最受傳頌的強片,勒賽的艱澀影像風格,卻獲主流商業媒體影評一面倒好評,電影充滿「人道主義」關懷的結局,映襯了電影沈浸感十足的「銳舞派對」(rave party)觀察紀錄與人性凝視。本片與尤沃金提爾《情感價值》(Sentimental Value)已經確定成為下半年所有影展搶著要的「大片」,奧斯卡前景可期。《穿越地獄之門》、《情感價值》能接續去年坎城出身《墜惡真相》、《艾諾拉》、《懼裂》、《璀璨女人夢》、《喵的奇幻漂流》,在票房與獎項上滿載而歸嗎?
關於《穿越地獄之門》,這也是記者私下最熱衷討論的電影。大家私下討論,現在誰還找得到「銳舞派對」(rave party)可去?我跟國際記者分享到,觀眾如我,解嚴前與解嚴後,因為階級身份、經濟與語言能力,無緣真正參與銳舞與嬉皮體驗,長大後比同輩菁英更遲,但仍嚮往柏林真正銳舞風景;此時,柏林「Bergham」已經傳說即將結束營業數次,就像是永遠不退休的宮崎駿,我們在等待結束的時刻。讓這部父子踏上尋找沈迷「沙漠謎漾派對」的中性性別氣質姊姊,卻最終迷失在沙漠的故事,在當下台灣的政治氛圍中,我們似乎也正在各種意義上,踏上沙漠尋找一場「看不見的派對」。

話說回來,「銳舞」的電子樂精神在全球各地開花,但在非洲、拉美或台灣「S2O」開出的花朵,可以被當作是高端菁英潮流電子樂,與素民接軌的案例嗎?《穿越地獄之門》肯定會是一部給台灣剛崛起的「音樂祭文化」青少年觀眾的真正電影體驗,但台灣的「藝術片」票房可以喚起多少「主流觀眾」的注意力?多少主流觀眾決心跳過那些「延遲」的風潮,直接喜歡眼前觸手可期的歡愉。就像短影音、魔芋爽、小紅書給年輕人的快樂。所以,誰(不)替這部片的票房擔心?
*
站在坎城影展總監(Thierry Frémaux)的立場,他關心的藝術電影末日,儘管可能就在這個夏天「總決戰」,或許也不能只用「台灣」一個地區的產業、政局、脈絡去定義。他恐怕不能料想,也沒能耐在此刻料想,明年此刻的光景。卻畫巴山夜雨時,僅是我輩青年影評人的感傷,但「末日」之夏,恐怕我已不能等到明年此刻才來盤點,與我切身相關的亞洲電影景況。
就像,坎城影展一結束,伊朗與以色列兩國間的爭執,差點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戰火一觸即發,但美國的強勢介入,火光才起就滅。韓國、日本的政壇氛圍也是詭譎萬變,電影拍攝需要時間,但我們只有當下。在台灣的我們,僅能看到、討論數個月內上映的國際電影,但這些電影籌劃、拍攝在數年之前,在年初首映,數個月後上映。國際藝術電影真的能反映當下亞洲局勢嗎?肯定可以。本文下篇,將繼續就伊朗的金棕櫚《It Was Just an Accident》切入,我們從該片電影內容,照見好萊塢與「反全球化」時代,在好萊塢與全球電影產業間漸大的鴻溝,以及這鴻溝在今天帶來電影「末日感」的緣由。
●作者:沈怡昕/影評人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不代表《NOWnews今日新聞》立場
●《今日廣場》歡迎來稿或參與討論,請附真實姓名及聯絡電話,文章歡迎寄至:[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