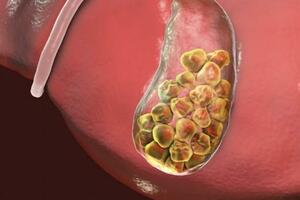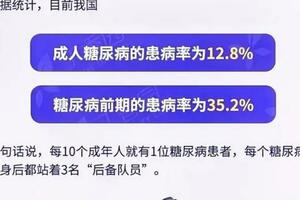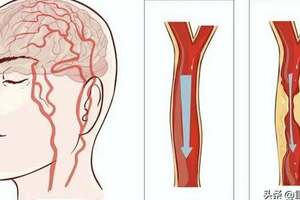右眼受損前的范曉蕾。 (受訪者供圖/圖)
一支針頭刺入自己的右眼,范曉蕾看不見它的模樣。
右眼玻璃體內的液體隨即被抽走,爾後,0.7毫升八氟丙烷氣體緩緩注入。時隔8年,范曉蕾已經忘記了氣體入眼時的感覺,卻記得注氣完畢,她看見了一團黑色的霧氣。
那團黑霧本該令她脫離的視網膜復位,然而,此後她卻在黑霧中越陷越深。
這不是一場複雜的治療。2015年9月,還是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的范曉蕾因右眼不適前往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就診,主治醫生推薦她前往一家私立醫院熙仁醫院接受氣術治療。意想不到的是,術後右眼疼痛,視力也由0.8逐步下降至0.02。
最初,范曉蕾以為,氣體質量問題是元兇。但當她發現涉事生產商實際只有工業用八氟丙烷生產資質時,她開始追究整個鏈條的責任:氣體生產、經銷商要為非醫療用氣進入醫院醫用負責;醫院則更應為使用非醫療品對患者施治負責。
從河北邢台走出、歷經10年苦讀方才走上北大教師崗位的范曉蕾自此開啟了人生中另一場漫長的「戰爭」。從2016年開始,她先後起訴了兩家涉事醫院、兩家八氟丙烷經銷商和一家生產商。一場訴訟耗時3年有餘,2019年海淀區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熙仁醫院使用的八氟丙烷氣體為非醫用氣體、非醫療產品,應承擔全部責任。北普及北氧公司在未取得八氟丙烷經營許可的情況下銷售該氣體,同樣存在過錯,兩公司承擔連帶責任。華特公司和北醫三院被認定無過錯。但范曉蕾並不滿意,繼續上訴,目前二審仍未有下文。
這本是一個不為多人知曉的故事。直到2023年3月,范曉蕾登上一個視頻自媒體的訪談節目,講述了8年來的經歷。有網友在這一走紅視頻下留言:當北大教師在面對醫療糾紛都如此困難之際,普通人又當如何自處?
視力0.02的世界
第一次知曉范曉蕾故事的人總會去看那隻受傷的右眼。
2023年3月,視頻自媒體「北京青年X壹次訪談錄」員工三三第一次見到范曉蕾時,特意盯著她的右眼看了一陣,「我好像看不出來跟我們正常人的眼睛有什麼大的區別」。
3個月後,當范曉蕾一身玫瑰紅的運動裝,坐在北大辦公室時,南方周末記者也努力觀察著她的右眼,試圖尋找那隻眼睛的不同之處。
這位39歲的北大中文系副教授留著齊脖頸的短髮,眼鏡鏡片後,右眼幾乎與常人無異,只是眼皮比左眼耷拉得稍多些,顯得有些「沉重」。
據范曉蕾的病歷及司法鑑定文書,2015至2016年間,她的右眼視力在0.1至0.03內波動。至2019年,其已降至0.02,范曉蕾形容,她的右眼眼前有光感,但看物如同隔著一片磨砂玻璃。
這個世界在她的眼中呈現出另一種樣貌:右眼剛受傷時,范曉蕾覺得眼前有一層塑料薄膜,看不真切。她常在半夜上廁所時閉上左眼,嘗試能否只用右眼看清衛生間瓷磚的紋路。8年後,薄膜遮擋的感覺減弱了很多,范曉蕾早已忘記右眼受傷前,那個正常的世界究竟長什麼樣。「醫生說,你脫離正常記憶很遠的時候,你會適應。就像一個小孩子,他生來看不見,就不會有任何痛苦。」
曾經開闊、清晰的世界已經在記憶中模糊,范曉蕾也漸漸習慣了另一種生活方式。白天裡,她依然要上課、批改作業、做科研,只是每當需要看電腦、寫文章時,她只在自然光下工作。她不信任燈光,擔心燈光頻閃會損害本就岌岌可危的眼睛。夜裡7點吃過晚飯後,她乾脆不再工作。閒暇時光里,她不看朋友圈,最近半年也才實名入駐微博。多數時候,她聽手機里播放的電視劇的聲音消遣,不過她更鍾愛聽手機講小說、傳記乃至醫療保健類的書,講「癌症怎麼產生的,我們為什麼要睡眠」。
范曉蕾至今沒有放棄挽救眼睛。每周,她都會去醫院做針灸、注射促進血液循環的藥物兩到三次。疫情期間,她曾有兩個月沒能做治療,眼睛便難以張開,看東西就難受。她估計餘生都將與這樣的治療為伴,而即便如此,這也只能延緩右眼情況的惡化。
注入右眼的0.7毫升氣體
2014年,在港科大獲得博士學位的范曉蕾回到了內地,並於次年在北大中文系謀得了助理教授的教職。從象牙塔到象牙塔的人生堪稱順遂,直到2015年9月。
范曉蕾記得,2015年9月4日,她第一次覺得右眼不舒服,有東西遮擋著她的視野。其病歷顯示,北醫三院主治醫生做出診斷——右眼孔源性視網膜脫離、左眼視網膜周邊變性,並給出了治療方案,即右眼玻璃體腔注氣術與雙眼底雷射治療。
當時,該醫生讓范曉蕾前往其坐診的熙仁醫院接受注氣術治療。病歷顯示,9月8日,范曉蕾去往熙仁醫院,右眼被注入0.7毫升八氟丙烷氣體。據後來的司法鑑定書,眼用八氟丙烷是一種惰性氣體,眼球內注入可使上皮細胞與視網膜感覺層牢固粘連,支撐視網膜復位,主要用於玻璃體切割、視網膜脫離等手術。

熙仁醫院。 (姜博文/圖)
范曉蕾回憶,術後「到第20天的時候,實在疼得不行」,她再次前往北醫三院複診。一審判決書顯示,9月28日當天,主診醫生將其帶往熙仁醫院抽出殘餘八氟丙烷氣體,並注入空氣恢復眼壓。
范曉蕾稱,此後她前往多家醫院眼科檢查。中國西苑醫院及協和醫院對其右眼的診斷均為「中毒性視網膜病變」,同仁醫院為「右視網膜脫離C3F8眼內注射術後缺血性右視神經病變」,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診斷為「右眼急性氣體致中毒性視網膜病變」。
雖然她跑了不少醫院,但大多數醫生都建議她找原醫生治療,唯一為她施治的,是當時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眼科醫生陶勇。陶勇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他印象里,范曉蕾前來就診時,右眼眼底的傷害是顯著的,對視功能造成了嚴重影響,但還沒到徹底失明的地步,「眼底病基本都是不可逆的致盲性疾病。眼底就像照相機的底片,損傷了最多只能部分好轉,或者阻止情況進一步變差,不可能完全恢復」。
知曉右眼再難恢復的范曉蕾決定找出問題。范曉蕾找到了為她注氣的醫生張曉麗,要求她告知氣體生產商是誰。2015年11月30日,張曉麗為她開具了一份診斷證明,證明寫道,該氣體的生產商為「廣東佛山市華特氣體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特公司)。
拿到該證明後,范曉蕾向當時的國家食藥監總局申請了信息公開。2016年2月,國家食藥監總局答覆,華特公司未有八氟丙烷或全氟丙烷產品按照醫療器械申請註冊並取得註冊證。
「我又去廣東華特網頁上查,發現廠商只能生產工業(八氟丙烷)產品。」范曉蕾說。她逐漸認定,華特公司的氣體是其右眼受傷的元兇。這令她感到憤怒:為什麼熙仁醫院會將無醫療用氣資質的華特產品用於醫療?
2023年6月15日,南方周末記者來到熙仁醫院,希望了解該院對這起糾紛的看法。醫務科一位負責人在6天後答覆稱,由於當年處理此事的人均已離開醫院,如今已經沒有人知曉當年的細節。也是在6月15日,南方周末記者在北京市另一家私立醫院見到了張曉麗,她婉拒了採訪。
艱難拉鋸的三年官司
八氟丙烷氣體從華特公司被銷售至熙仁醫院的鏈條如今已然清晰。
海淀區法院在一審時認定,華特公司向北京市北氧特種氣體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北氧公司)銷售前述氣體一鋼瓶,後者又銷售給北京北普飛龍氣體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北普公司),熙仁從北普公司購進該瓶氣體。
在協商未果之後,2016年8月,范曉蕾以侵權責任為案由,起訴熙仁醫院及華特公司,要求賠禮道歉,賠償現有損失5萬元,支付懲罰性賠償15萬元,而傷殘賠償金等需在傷殘鑑定完成後確定。她回憶,2016年首次開庭後,她追加了北醫三院作為被告,而熙仁醫院則先後追加了北普及北氧公司作為被告。被告最終增加到五方之多。
北京市煒衡律師事務所律師殷梓介曾在2016-2017年擔任過范曉蕾的代理人。他的判斷是,范曉蕾所認定的熙仁醫院將工業用氣用作醫療器械「在法律上應該是站得住腳的」,她此前收集的證據也較為充足。接替殷梓介成為一審階段最後一位代理人的醫療法律專家卓小勤也如此認為。
但三年多的庭審對范曉蕾而言依然是一場艱難的拉鋸。
一審判決書顯示,北醫三院認為其未對范曉蕾實施轉診行為,是因醫院當時無玻璃體注氣條件,故建議患者去其它醫院治療。熙仁醫院則稱,范曉蕾所述損害是熙仁診療的後果缺乏依據,這是其病情自然轉歸的結果,與醫療行為無關。范曉蕾所述的八氟丙烷氣體缺陷問題,應承擔舉證責任並通過鑑定確定。
儘管涉事醫生張曉麗承認使用了有華特公司生產標識的鋼瓶,但華特公司認為,案件尚無充分證據證明範曉蕾所使用氣體為華特生產。即便熙仁使用了華特氣體治療范曉蕾,損害後果也不應由華特承擔,因為從產品包裝、外觀、用途上可判斷其非醫療產品。另外,華特公司未將八氟丙烷用作醫用氣體銷售。
北普公司辯稱,其同意華特的答辯意見,熙仁給范曉蕾帶來的傷害應由熙仁承擔責任。北氧公司則辯稱,其非氣體生產商,也不知北普公司將氣體賣給熙仁,不應承擔責任。
直到2019年,幾方爭執的焦點才得到第三方機構的鑑定。北京市民生物證科學司法鑑定所出具的鑑定文書認定,北醫三院診療過程符合診療常規,導致患者出現右眼視力下降損害後果的原因,除與自身疾病的不良轉歸有關,不排除與醫方為其注入的八氟丙烷氣體不良反應有關聯,可認定熙仁醫院存在過錯,在導致范曉蕾損害後果中的原因力程度可鑑定為主要原因。
提供希望的北大資源
范曉蕾記得,訪談視頻播出後,曾有人給她留言,感嘆她作為一名北大老師維權都如此艱難。
博士學歷、任教燕園的確令范曉蕾在訴訟中比普通人多了些優勢,然而,象牙塔內外的巨大反差也令糾紛中的人與事顯得更為複雜。
殷梓介的印象中,范曉蕾有著較真、嚴肅的一面,案件細節摳得尤其仔細。為了打贏這場訴訟,范曉蕾以做學術研究的方式鑽研法條、搜集證據,就連她的母親陳幽雲——一位中專學歷的退休校醫也加入進來。在研讀了兩部法律書後,陳幽雲認為自己摳出了要求懲罰性賠償的可能。
「較真」性格也有另一面。「知識分子有時候主意也比較大。」卓小勤對此也有感觸。范曉蕾曾堅持申請對熙仁醫院的部分財產做財產保全,擔心醫院倒閉無法賠償。卓小勤勸過她,但范曉蕾還是堅持己見。
律師也要精心選擇。范曉蕾讀研期間導師、北大中文系教授郭銳覺得,范曉蕾信不過別人,律師接觸了不下10個。但范曉蕾有她的理由:有朋友推薦來的「律師」最後被她查出實際不是律師;有律師說熙仁醫院無責,責任是氣體生產商的;也有律師甚至不了解什麼是懲罰性賠償。
她也竭盡全力挖掘著北大可能連通的人脈資源。卓小勤是一位北大教授介紹的——那是范曉蕾上中學時在《今日說法》節目上常看到的嘉賓;她還向北大化院的博士諮詢過「工業用八氟丙烷」各個成分的作用。證據清單里涉及化學品的學術文獻資料,亦是化院博士提供的。
北大的教職也為她提供了一份生活保障:右眼出事後,范曉蕾曾休息了半年,但在此期間,她的工資並未停發。
這並非普通人能輕易獲得的。即便如此,庭辯遭遇還是能讓她「肝氣鬱結」很多天。陳幽雲自女兒出事後,從邢台趕來北京照料她。她的印象中,女兒曾經溫順、聽話,但身陷訴訟的頭幾年,常無緣無故發脾氣,「有時候還想跟你干架」。半夜裡,她都曾聽到過女兒的喊叫。
在范曉蕾右眼出事後一個模糊不清的年份,北大中文系教授詹衛東記得:一天晚上,范曉蕾在上課時忽然暈倒。救護車到達以後,他陪著范曉蕾去了北醫三院。他能察覺到,那時的范曉蕾身體特別虛弱。
范曉蕾形容那次暈倒是直直地倒下去,磕出了輕微腦震盪。出事後的幾年時光里,因為過度使用左眼,范曉蕾在梳頭時總覺左半邊頭疼,她還總愛往左邊跌倒,左肩和左臂一到冬天或是疲勞時就麻木、疼痛。醫生曾擔心是她腦部神經受到氣體的影響,讓她去查查,可她沒去。
她害怕真查出什麼事來。
最絕望的時刻
郭銳記得,2020年元旦,范曉蕾接到了一審判決書寄到住處的電話。那時,她正在昌平吃涮羊肉,餐館「前不著村後不著店」,但她卻堅持要立刻走。
海淀區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同時判定熙仁醫院賠償范曉蕾營養費4500元、精神撫慰金30000元,北普、北氧公司對賠償承擔連帶責任。
熙仁醫院遞交了上訴狀,范曉蕾也上訴了,她並不滿意,尤其是法院並未支持懲罰性賠償的訴請。目前官司暫無下文。
南方周末記者向熙仁醫院詢問案件進展,該醫院醫務科負責人答覆,當年處理此事的人均已不在醫院工作,她只知道案件已經完結,賠償也已經到位。
范曉蕾則稱,她至今未收到賠償,對二審也已不甚在意。她開始考慮刑事控告,認為熙仁醫院涉嫌「銷售不符合標準的醫用器材罪」,希望讓其承擔刑事責任。
這並非易事。郭銳向南方周末記者坦承,他認為醫院並非故意害范曉蕾,也可能並不知道使用的是非醫療用品,何必非要刑事控告?但范曉蕾始終有自己的主意:「首先我有一個想法,我要有一大堆依據,我把我的依據論證好,我的觀點是對的,我就會堅持。我不是會搖擺的那種人。」
2021年,范曉蕾通過考核,成為長聘副教授。生活穩定下來後,她有了更多精力處理糾紛。2023年2月,范曉蕾見到了一位朋友,聊起右眼受傷的舊事時不由落淚。朋友建議她將此事公之於眾,會對心理有療愈作用。通過朋友的引薦,她找到了前述自媒體。2023年5月,視頻播出後,在B站就有近兩百萬播放,評論也累積了四千多條。

范曉蕾在視頻節目裡講述維權故事。 (視頻截圖/圖)
因為這段訪談,甚至多年失聯的朋友紛紛向她表達敬佩,但范曉蕾卻覺得,視頻播出後是她最絕望的時刻。她不能單刀直入地講述自己的傷害,反而還要敘述勵志治學的經歷,實在有些心酸。她難免想到更多有類似經歷的普通人,假如他們沒有北大老師的身份,沒有右眼受傷後仍鑽研學術的經歷,而是一開始就被打垮了,他們要怎樣講出自己的故事?
評論區里,不少人也分享了自己的醫療糾紛故事,卓小勤對此深有感觸,人們平常遭遇醫療糾紛,怨氣難以化解,此次看到范曉蕾的故事,仿佛找到了發泄口。
如今,范曉蕾正在尋找合適的時機報案。如果刑事控告不成,她希望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把經歷寫成一部書,就像自己已經出版的學術專著一樣,傳諸後世。
(文中陳幽云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姜博文